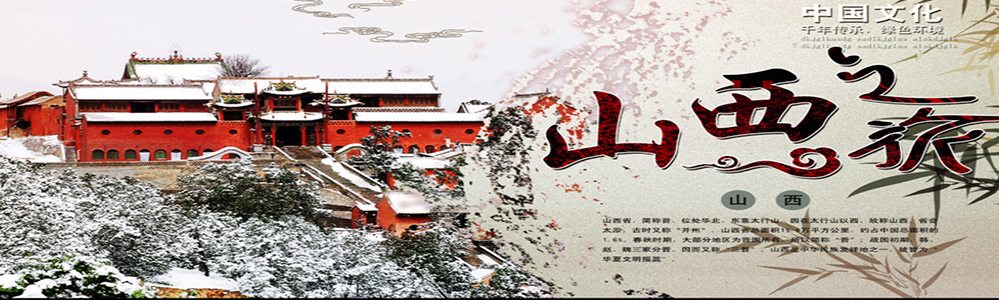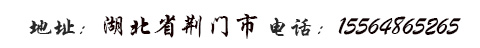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山西人文化性格的双重
|
众所周知,山西人杰地灵、历史辉煌,而且祖上曾阔过。 且不说山西在文学家柳宗元的笔下曾被冠以“表里山河”的美誉,毛泽东曾当着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面给出“裴姓出山西”、“天下无二裴”的褒奖; 也不说在土皇帝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曾经是全国的模范省份,在抗日战争中山西作为八路军三大主力的活动中心一度成为抵抗日军的主战场; 更不论文化学者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对富可敌国的晋商的推崇之至,北大教授韩毓海先生对当代山西何以失去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地位进行的深度剖析; 还不论山西籍作家李琳之曾以“中国,你欠山西一声对不起”的帖子在网上走红,山西官员曾以山西“不东不西,不是东西”戏谑并在坊间传为笑谈。 凡此种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便是一个多面的山西、立体的山西,一个五味杂陈的山西、一个欲说还休的山西。 一定意义上讲,无论是山西的昨天还是山西的今天,都是山西人的性格使然。山西人的性格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双重性,解读山西人性格在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文化特征,对于山西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强省都有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代山西人应适应市场经济和转型社会的要求,坚持立足山西、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原则,以实现山西人性格的再造与重塑。 1 山西人性格研究的范畴本文所讨论的山西人既非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也非个别意义上的山西人,而是特殊意义上的山西人,即是说以长期生活、学习、工作在山西的特定人群作为山西人的考察对象,这种研究既不同于一般人类学语境下的宏观研究,也不同于旨在寻求个别心理特征和性格结构的微观研究,而是就特定人群的文化生态所作的中观研究。 在历史与现实的反差中,在现象与本质的交织中,通过对山西人性格的批判性反思,来探索山西人性格重塑与再造的话语转换与时代变奏。 2 山西人性格的地理文化差异首先,山西人作为中国人,无疑具有一般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与以海洋文明和工商业文明为标志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则以农业文明和大陆文明而著称于世。就中国人而论,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一书中把中国人的性格总结为八句话:老成敦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诙谐,因循守旧。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则认为中国、西方和印度分别代表了人类生活方式的三种不同路向:持中的、向前的和向后的路向。鲁迅则在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中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和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还讲过北方人的缺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的缺点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更是把一些中国人讥之为“酱缸蛆”,可谓是击中肯綮。 其次,山西人作为中国的北方人,又具有北方人的性格特征。就中国的南北方而言,北方往往意味着干旱、寒冷、贫瘠、强悍和壮阔,南方则成为温暖、湿润、富庶、发达、柔婉、清丽的同义语。孕育中华文明的两大河流黄河和长江也不同,一则以雄浑著称,一则以清奇见长。梁启超主张“南老北孔”:哲学上儒家成为北方文化的主流代表,道家则反映了南方文化的精神气质。追求逍遥自由超拔飘逸的老庄和屈子,与崇尚礼乐教化仁和中庸的孔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国维认为,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玄想,北方人重实行;北方人有体格缺智力,南方人则有智力缺体格。 最后,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山西人多山性少水性的性格特点。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的东部,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北有恒山、五台山,南有中条山。山地面积约占70/。山多水少,水资源严重缺乏,因而山西人的性格多山性少水性(如多稳定性少流动性,多原则性少灵活性,多封闭性少开放性,多儒家传统少道家思想,多质朴少浮华等)。山西人的性格基本上都是由此决定和派生的:高山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使人们视野狭窄;交通闭塞又使得人们信息封闭,内外交往不发达;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农耕生活,使他们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守土不离乡,安土重迁,恋家爱乡,成为挥之不去的不老情结,流进血液注入骨髓,使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生态无不打上了鲜明的黄土地烙印,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正如孔子所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智者如行云流水,变动不居,周流无滞,快乐无比;仁者似崇山峻岭,厚重不迁,高不可攀,万寿无疆。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得也是山的无私性和水的兼容性。以山水喻人性,可谓是形象贴切又逼真。 当然,同样是山西人,由于受亚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出明显的年龄性、职业性和地域性,如晋北人粗犷尚武,晋中人精明重商,晋南人礼让文雅等。 3 山西人性格的历史文化特征近年来,学者们在山西地方文化的研究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产生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刘纬毅先生认为,山西文化有四大特色:民族融合性,兼容并包性,地域差异性,黜华尚实性。 李元庆先生认为三晋文化的精华在于: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在与外来文化交流时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和适应性,在受其它地域文化冲击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 程人乾教授认为,历史上山西人的性格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在历代文人及其作品中又外化为豪爽开朗与细致入微的双重性,其中外向开拓的一面又突出表现为坚忍不拔的创业能力和海纳百川的融合能力。前者如晋文公重耳流浪在外19年,后励精图治终成霸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车战向马战转变的先河,以及晋北村民背井离乡“走西口”和晋南明初洪洞大槐树大规模的人口外迁。后者如汉民族在先秦时与戎狄、秦汉魏晋时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辽宋夏金元时与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长期征战中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最早开发的省份之一,是中国远古人类生息繁衍之地。史书记载:“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有禹王城,河津有禹门口,芮城有大禹渡)”山西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关公文化、帝王文化、民间工艺文化、建筑文化、晋商文化、戏曲文化、歌舞文化、边塞文化、红色文化等),地上文物居全国之首。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认为“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山西西临黄河,东凭太行,自古以来就有表里河山之称,境内关隘棋布,岭渡星罗,进可攻,退可守,进退有据,伸屈自如,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大小王朝的起家之地,如大唐皇帝李渊父子,后唐皇帝李存勖,后晋皇帝石敬瑭,后汉皇帝刘知远,北魏皇帝拓拔圭、拓拔宏以及民国军阀阎锡山等都是以其为据点并成就霸业的。 简言之,在中国历史上,山西地区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通道,一度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之地,如朔州右玉的杀虎(胡)口,朔州怀仁的金沙滩等都是这段风云际会的历史见证。而且,无论是定都长安的汉帝国还是唐王朝,也无论是定都北京时的元明清,山西都是作为扼守和护佑帝都的京畿重地而为历代统治者所亲睐和看重。 总之,历史上山西人的性格特征以外向开拓为主,是健康的向上的。其积极性的一面有:睿智、中庸、宽容、忍耐、节俭、善于经商理财、适应性强等,消极的一面有:封闭保守、安土重迁、土气、小气等。 4 山西人性格的经济文化研究“三晋之风勤与俭”,山西人有老醯(音同西)儿之称,爱吃醋,喜面食,早晚不离小米稀饭,饮食简单不时尚。他们乐天知命,本分矜持,安分守已,循规蹈矩,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使他们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克勤克俭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主要生存法宝,土气、小气的习性也就在所难免。典型的山西人,以勤俭、善理财、眷恋家乡而著称。几乎所有的县志在民风民俗方面的记载中,都有本县人勤俭之说。例如乾隆时所修《孝义县志》便称孝义“民用俭约”,年所修《翼城县志》也称翼城人“黜浮华,崇质朴,翼古风也。” 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会经商,善理财,是山西人经济文化的真实写照。明清时期“富甲中国五百年”、“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晋商,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新中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汇通天下”而著称、足迹遍布海内外的晋商在经营理念、价值取向上一反儒家正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转而奉行具有明显超前性和现代性的“学而优则贾”精神,在经济文化观上确实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里程碑式的意义。经商之道是薄利多销、诚信为本,理财之道是开源节流、精打细算。一度时期享誉全国的山西文学流派——由赵树理开创的以西、李、马、胡、孙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山西地域文化的经济特征和地方特色。 有人说,山西恐怕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道堡垒。在山西,国有企业数量多规模大,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撑起了山西经济的半壁江山。山西富有集体经济传统,汾阳的贾家庄、昔阳的大赛、平顺的西沟,在毛泽东时代便是农村经济的一面旗帜。 山西也极富奉献意识与牺牲精神,作为产煤大省,如同煤“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一样,山西也颇具煤的品格,外表上给人以“傻大黑粗”形象不佳的感觉,然而内里却隐韧笃定、朴实无华,大有“丑小鸭”蜕变为“美天鹅”的气魄。 不可否认,山西经济至今仍残留着农业文明的传统烙印,尤其是北方一些农村,村民们仍然恪守着“咋个好出门不如赖在家”的古训,一到农闲的冬日便三五成群地在大街上扎堆晒暖暖、当“太阳花”,赚个身闲心也闲,悠哉游哉活神仙。还要承认,一方面,富人文化即富裕起来的人不懂得回报社会,而是富起来后到北上广甚至海外置地买房逍遥自在休管身后洪水滔天,另一方面穷人文化即贫穷之人由于单纯等、靠、要心理的作怪,不仅物质贫困,更重要的是精神、思想、文化上也贫困,这两方面因素的叠加,成为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 大致来看,无论是局外人还是本省人,对山西人的评价是有褒之有贬之,有扬之有抑之,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参杂混合,赞成者认为山西人不乏幽默,亲和力强,说话直率、办事认真、守信践行,易于同人相处并得到信任,反对者认为山西人“又黑又脏”,封闭保守不开放,贫穷落后不现代,且爱面子、不守时、不讲公德。对山西人要作出一个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实属不易。 5 山西人性格的再造与重塑明眼人都知道,山西一些人总是热衷于谈论自己的过去,沉浸在昔日的辉煌中喜不自胜、不能自拔。在山西旅游界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说是在中国,五十年的中国看深圳,一百年的中国看上海,一千年的中国看北京,三千年的中国看陕西,五千年的中国看山西!着实令山西人扬眉吐气、高兴了一阵子。网上还流行着一个帖子,以“你说山西没有×××,×××就笑了”为题,着实火了一把。如你说山西没有史学家,司马光就笑了;你说山西没有女皇帝,武则天就笑了;你说山西没有高僧,法显就笑了;你说山西没有十大元帅,徐向前就笑了;你说山西没有歌唱家,郭兰英(阎维文、谭晶)就笑了;你说山西没有电影导演,贾樟柯就笑了;你说山西没有改革家,吕日周就笑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然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果老是回忆过去,老讲祖上的事情,老谈昔日的荣光,便是一种不健康的、不思进取的、消极颓废的心态在作祟。如果这种向后看的心态一旦成为社会大众的主流心态,那必然意味着人们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失落感、落魄感,只能昭示着对曾经过往的流连忘返、心向往之,对现实处境的暗然神伤、无可奈何,对未来前景的噤若寒蝉、讳莫如深。伴随着经济指标的断崖式下滑以及政治生态的系统性坍塌,可以说在当前山西官民心中普遍弥漫着一种少有的不自信、挫败感和失落感,这已成为阻碍山西发展的一大心理障碍和精神负担。 山西经济社会要转型根本上有赖于山西人的思想转型、文化转型、性格转型。改革开放之初,山西处于观望等待的心理,未能及时从“左”倾思潮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没有赶上第一波思想解放的潮流,落下步来。接着是沿袭老式工业化的路子,挖煤、输电、修路、架桥,虽换来了经济的一时发展,然付出的代价也不小,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经济发展没有后劲。新世纪伊始省委省政府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效果明显,如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举办“华夏文明看山西”系列活动和各种名目的文化节等。 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资金和人才,影响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都需要改变。为此,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着力: 一是要坚持立足山西、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原则。从挖煤到挖文化,从文化自觉到文化强省,从中部崛起到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从综改试验区到再造一个新山西,山西人正在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浪潮中,逐渐地找准方位、站稳脚跟、认识自身、超越自我。 二是要完成“两个转变”: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转变,从官场人格向市场人格的转变。制约山西发展的两大性格缺陷:传统人格的烙印太深,官场人格的思想太重。恩格斯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源远流长、丰富厚重、复杂多变的传统历史文化就象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就可成为当代山西人重振旗鼓、再铸辉煌的精神财富,运用不好则有可能成为山西人低迷失落、裹足不前的思想枷锁。 三是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应实现“三个转向”:干部从“只唯上不唯下”转向群众路线,知识分子从“只唯书不唯实”转向理论联系实际,群众从“只好分不好合”转向互助合作。 上述三条我们必须深长思之,作出选择。 责编:彦利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nxishengzx.com/sxzw/8634.html
- 上一篇文章: 朔州无牌警车招摇过市,谁给的特权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